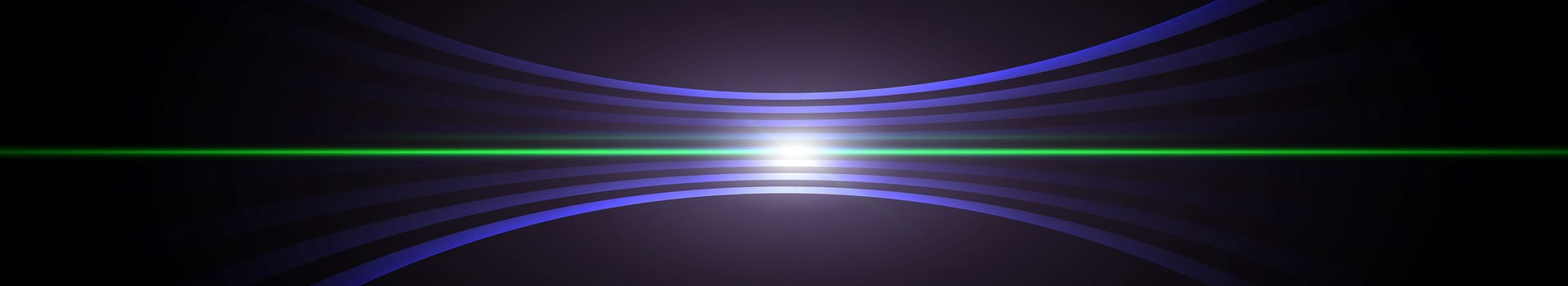
01
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,北京,天安门广场。
人潮如海,红旗漫卷。
在城楼西北角的一间临时改造的播音室里,空气仿佛凝固了。
这里是新中国的心脏,即将向全世界发出第一声啼鸣。
瞿独伊坐在麦克风前,感觉自己的心跳声比窗外鼎沸的人声还要响亮。
灯光下,她清秀的面庞显得有些苍白,握着俄文广播稿的手指,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。
房间很小,挤满了机器和工作人员,线路如同蛛网般缠绕在地板上。
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机器预热后特有的、混杂着尘埃的灼热气味。
「各单位注意,倒计时五分钟。」
导播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,冷静得没有一丝波澜。
瞿独伊深吸一口气,试图平复内心的波涛。
她只有28岁,但此刻,她肩上扛着的,是四万万同胞的期盼,是一个饱经磨难的民族向世界发出的宣言。
她的任务,是用俄语,将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宣告,同步广播给苏联,广播给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。
这是命令,是荣耀,更是千钧重担。
她又检查了一遍桌上的稿件,那是她熬了几个通宵翻译、校对、润色的最终版本。
每一个词,每一个音节,都必须精准无误。
窗外,毛主席洪亮而带着湖南口音的声音,通过扩音器隐隐传来,穿透了墙壁,震撼着广场,也震撼着她的耳膜。
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,今天成立了!」
就是这一句。
瞿独伊的眼睛瞬间湿润了。
一瞬间,无数张面孔,无数段往事,如同潮水般涌上她的心头。
父亲瞿秋白的身影,在记忆深处是那样清晰。
那个温文尔雅、戴着圆眼镜的知识分子,那个在上海大学讲台上挥洒自如的师长,那个在她童年时,用温暖的大手牵着她,教她认第一个俄文字母的慈父。
她仿佛又回到了莫斯科郊外的那栋小楼,父亲灯下写作的背影,母亲杨之华温柔的叮咛。
可那一切,都永远地定格在了1935年的那个春天。
噩耗从遥远的祖国传来,像一把淬了冰的利刃,刺穿了她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里所有关于未来的幻想。
那一年,她才14岁。
此后,是漫长的等待,是与母亲在异国他乡的相依为命,是踏上归国路途的欣喜,更是堕入新疆军阀盛世才黑牢的四年绝望。
铁窗,镣铐,严酷的审讯,同志们的牺牲……
一幕一幕,都烙印在她的生命里。
而现在,她坐在这里,坐在新中国成立大典的播音室里,要用父亲教给她的语言,向世界宣告这个他曾为之奋斗、为之牺牲的理想,终于实现了。
这何尝不是一种告慰?
「瞿独伊同志,准备。」
耳机里传来指令,将她从汹涌的回忆中拉回现实。
她眨了眨眼,将泪水逼了回去,目光重新聚焦在稿件上。
她知道,现在不是感怀的时候。
她拿起笔,在稿件的开头,重重地写下了一个词:「Начинаем」(我们开始)。
这是她对自己下达的命令。
扩音器里,仪式的进程在继续。
瞿独伊的全部心神,都集中在耳朵和喉咙上。
她像一头蓄势待发的猎豹,等待着那个属于她的时刻。
终于,耳机里传来了那个期待已久的指令。
「俄语广播,现在开始!」
瞿独伊按下了面前一个红色的按钮,对着麦克风,用清晰、标准、但略带一丝颤抖的莫斯科口音,开始了广播。
「Говорит Пекин……」
「这里是北京……」
声音通过电波,瞬间跨越了千山万水,飞向了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,飞向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。
她全神贯注,每一个发音都力求完美。
然而,当第一段播送完毕,利用一个短暂的间歇,她回放录音时,眉头却紧紧地锁了起来。
不行。
她在心里对自己说。
太紧张了,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,情感的控制也不够到位。
这不仅仅是一份新闻稿,这是一份历史的宣言。
它应该充满力量,充满自信,充满一个新国家诞生时的骄傲与喜悦。
而她的第一遍播音,显然没有达到这个要求。
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。
广场上的庆典还在继续。

她如果要求重来,会不会打乱整个广播流程?会不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播出事故?
导播和其他工作人员都看着她,眼神里充满了疑问。
在如此重大的直播中,一个播音员对自己刚刚完成的工作表示不满意,这是一个极度罕见、也极度冒险的情况。
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
瞿独伊做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始料未及的决定。
她按住通话键,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对导播说:
「刚刚的录音作废,我要重新录第二遍。请立刻给我准备。」
02
这个决定,在当时那个气氛紧张到极致的播音室里,无异于投下了一枚炸弹。
所有人都愣住了。
要知道,这并非一次普通的录播,而是与开国大典进程紧密相连的半直播。
每一个环节的时间都经过了精确计算,环环相扣。
重录一遍,意味着要打乱既定的时间表,后续的环节也可能受到影响。
更重要的是,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。
如果第二遍录音出现任何差错,或者因为时间延误而错过了关键的播送节点,这个责任谁也承担不起。
导播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,他看着瞿独伊坚定的眼神,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应。
他很清楚眼前这个年轻女同志的背景,她是烈士之女,是从新疆监狱里走出来的革命者,她的俄语水平在新华社乃至整个北京城都无人能及。
但背景和能力,并不能成为此刻冒险的理由。
「独伊同志,」导播的声音有些干涩,「时间很紧张,第一遍……我觉得已经很好了。」
这是一种委婉的拒绝。
瞿独伊摇了摇头,她的目光没有丝毫动摇。
「不,不好。」
她一字一句地说道。
「这不是我最好的水平,更不配得上今天的这个日子。声音里的情绪不对,那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,没有完全表达出来。」
她停顿了一下,视线扫过房间里每一个人的脸。
「请同志们相信我,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保证,第二遍会更好,而且不会耽误后面的播送。」
她的声音不大,但异常清晰,带着一种与她年龄不相称的沉稳和决断。
这种决断,是在莫斯科的寒冬里磨砺出来的,是在新疆的牢狱中锤炼出来的。
那是一种经历过生死考验后,才会拥有的从容和坚定。
播音室里一片寂静,只能听到机器发出的轻微嗡嗡声。
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瞿独伊和导播之间。
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拉长了。
最终,是导播先败下阵来。
他从瞿独伊的眼神里,看到了一种无法拒绝的东西。
那是一种对信仰的虔诚,一种对完美的极致追求。
他咬了咬牙,做出了决定。
「好!我同意!」
他拿起通话器,对技术人员下达指令。
「各单位注意,俄语广播重新录制,准备清空磁带,所有人保持安静!」
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又紧张了起来。
瞿独伊再次坐到麦克风前,这一次,她的内心反而平静了下来。
她闭上眼睛,调整着自己的呼吸。
脑海里再次浮现出父亲的模样。
她想起父亲在《多余的话》里写下的那些文字,那些对革命理想的坚守与反思。
她想起在新疆监狱里,母亲杨之华对她和同志们的鼓励:「要活下去,要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。」
她想起那些在黎明前牺牲的战友,他们甚至没能看到今天广场上飘扬的红旗。
所有的情感,所有的记忆,此刻都汇聚成了胸中的一股热流。
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,眼神里的紧张和不安已经褪去,取而代代的是一种深邃的、饱含历史厚重感的光芒。
她朝导播点了点头。
第二次录音,开始了。
「Говорит Пекин……」
「这里是北京……」
同样的一句话,从她口中再次响起时,已经完全不同了。
她的声音沉稳、有力,充满了自信和喜悦,每一个音节都像是用金石镌刻而成,带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那声音里,有一个女儿对父亲的告慰,有一个革命者对理想的礼赞,有一个新中国公民对未来的无限憧憬。
在场的所有人,都被这声音深深地感染了。
他们仿佛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年轻的播音员,而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,在用她的声音,向全世界讲述一个古老民族的浴火重生。
这一次的录音,一气呵成,完美无瑕。
当最后一个单词落下,瞿独伊才缓缓地靠在椅背上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她感到一阵虚脱,仿佛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。

但她的内心,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安宁。
最终,正是这第二遍录音,通过强大的电波,传遍了世界。
它成为了许多国家,许多人听到的,关于新中国的第一个声音。
这个声音背后的波折,以及那个在关键时刻,敢于坚持,敢于承担责任的年轻女播音员,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都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
而这个看似寻常又不寻常的家庭,背后牵连的,却是我党早期一段波澜壮阔而又充满悲欢离合的隐秘历史。
这个故事,要从瞿独伊的母亲,那位名叫杨之华的奇女子说起。
03
故事的起点,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。
那是一个风云际会、思潮激荡的时代。
彼时的杨之华,是一个挣扎在旧时代婚姻牢笼里的新女性。
她出生于浙江萧山的一个士绅家庭,接受了良好的教育,心中充满了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。
然而,家庭为她安排了一桩门当户对的婚事,丈夫名叫沈剑龙,是浙江有名的大户人家的子弟。
沈剑龙并非恶人,他同样才华横溢,但两个在精神世界上无法同步的年轻人,被硬生生地捆绑在一起,婚姻生活充满了压抑和苦闷。
杨之华不甘心就这样被困在深宅大院里,了此一生。
她生下女儿沈晓光(也就是后来的瞿独伊)后,内心反抗的火焰燃烧得更加猛烈。
她要做一个独立的人,而不是谁的附庸。
1923年,她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决定:冲破家庭的阻挠,考入了国共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。
这个决定,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,也改变了她女儿的一生。
上海大学,在当时是革命思想的摇篮,汇聚了一大批顶尖的红色学者。
而社会学系的系主任,正是时年25岁,却早已声名鹊起的瞿秋白。
瞿秋白,江苏常州人,才华横溢,风度翩翩。
他精通俄语,是最早一批系统向国内介绍苏俄情况的理论家,他的文章,像一道道划破暗夜的闪电,启迪了无数在黑暗中摸索的年轻人。
在课堂上,杨之华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人物。
他站在讲台上,戴着一副圆眼镜,镜片后的目光深邃而明亮。
他讲授的不是枯燥的理论,而是结合中国社会现实,剖析革命的未来。
他的声音不高,但充满激情和逻辑的力量,每一个字都敲击在杨之(华)的心坎上。
杨之华像一块干涸的海绵,疯狂地吸收着这些全新的知识和思想。
她开始明白,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,真正的妇女解放,只有在整个社会得到解放的时候才能实现。
她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活动,很快就成为了学生中的活跃分子。
她的聪慧、勇敢和对理想的执着,也引起了瞿秋白的注意。
在一次次的讨论和交流中,两颗追求共同理想的心,越走越近。
他们谈论革命,谈论文学,谈论俄国的诗歌,谈论中国的未来。
瞿秋白发现,眼前这个女子,不仅有美丽的外表,更有一个丰富而坚韧的灵魂。
而杨之华也发现,这位年轻的系主任,褪去学者和革命家的光环后,内心是那样的细腻和热情。
一种超越了师生情谊的情愫,在两人之间悄然滋生。
然而,横亘在他们面前的,是杨之华尚未解除的婚姻。
在那个时代,一个已婚已育的女性,想要挣脱婚姻的枷锁,去追求新的爱情,需要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和道德审判。
但杨之华的性格中,从不缺乏抗争的勇气。
她决定回到浙江,与丈夫沈剑龙摊牌。
她以为这会是一场激烈的争吵,甚至是一场无法收场的冲突。
但事情的发展,却大大出乎了她的意料。
沈剑龙,这位旧时代的士绅子弟,在听完杨之华坦诚地讲述了她在上海的经历、思想的转变以及与瞿秋白的情感后,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。
他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妻子,她的眼睛里闪烁着他从未见过的光芒,那是一种对新世界的向往。
他知道,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她。
或许是出于对杨之华的尊重,又或许是内心深处同样存有的一丝新思想的触动,沈剑龙最终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。
他同意离婚。
不仅如此,他还提出,要亲自去上海,见一见那个叫瞿秋白的男人。
这个场景,充满了历史的戏剧性。
1924年,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,同时刊登了三则启事。
第一则是杨之华与沈剑龙解除婚姻关系的启事。
第二则是瞿秋白与杨之华宣布结合的启事。
第三则,也是最令人称奇的一则,是沈剑龙与瞿秋白共同署名的启事,宣布他们二人结为挚友。
在瞿秋白和杨之华的婚礼上,沈剑龙真的到场了。
他不仅送上了诚挚的祝福,还把年幼的女儿沈晓光,正式托付给了瞿秋白。
他对瞿秋白说:
「之华,我就把她交给你了。晓光,也拜托你了。」
瞿秋白紧紧握住他的手,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这场堪称“文明离婚”的事件,在当时的上海滩引起了不小的轰动,也成为了后来许多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。
婚礼之后,沈晓光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。
1925年,瞿秋白为她改名为“瞿独伊”。

“独伊”,取“独一无二”之意,寄托了他对这个继女视若己出的疼爱和期望。
瞿秋白一生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女,瞿独伊,便成为了他唯一的女儿。
他用全部的父爱,去弥补这个孩子童年缺失的一角。
他教她读书,教她说俄语,给她讲革命的道理。
在瞿独伊的记忆里,这位继父身上,没有丝毫严厉和说教,只有无尽的温和与耐心。
那个家,虽然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而时常搬迁,却总是充满了书香和温暖的笑声。
然而,这样温馨的时光,在历史的洪流面前,注定是短暂的。
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严峻,瞿秋白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。
1928年,作为我党重要的领导人之一,他需要前往莫斯科,参加重要的会议。
这一次,他和杨之华做了一个决定:带上年仅7岁的瞿独伊,一同前往那个红色的国度。
他们未曾想到,这一去,竟是父女之间最后的、完整的相处时光。
莫斯科的白雪,见证了一个中国革命家庭短暂的团聚,也预示着一场更为漫长和残酷的分别,即将到来。
04
莫斯科的冬天,来得特别早。
漫天的白雪覆盖了这座城市,红色的克里姆林宫尖顶在白雪的映衬下,显得格外醒目。
对于7岁的瞿独伊来说,这里的一切都是新奇的。
她第一次见到如此厚重的大雪,第一次穿上笨重的毡靴,第一次听着周围的人们说着父亲教给她的那种奇特的语言。
瞿秋白和杨之华在莫斯科的工作异常繁忙。
他们被安排住在一栋分配给各国共产党代表的公寓里,每天早出晚归。
瞿独伊大部分时间,都是一个人在房间里,透过结着冰花的窗户,看着外面陌生的世界。
很快,瞿秋白夫妇就意识到,这样的环境不利于孩子的成长。
经过慎重考虑,他们做出了一个在当时许多革命者都会做出的选择——将女儿送进著名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。
这所儿童院,由苏联政府创办,专门接收和培养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子女。
这里像是一个小小的“红色联合国”,孩子们来自德国、西班牙、保加利亚、中国……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,有着不同的肤色,但他们的父辈,都有着共同的信仰。
将女儿送走的那一天,杨之华的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。
瞿秋白则蹲下身,一遍遍地整理着女儿的衣领,轻声嘱咐她:
「独伊,在这里要听老师的话,要和同学们团结。爸爸妈妈会经常来看你的。」
年幼的瞿独伊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她并不知道,这句“经常来看你”的承诺,在未来的岁月里,会变得多么奢侈。
伊万诺沃的生活是集体化的,也是军事化的。
孩子们每天要按时起床、操练、学习。
课程除了常规的文化课,还有大量的政治教育,以及各种生产技能的培训。
对于一个从小在父母呵护下长大的孩子来说,这种突然的转变是艰难的。
瞿独伊常常会在夜里,因为思念父母而偷偷哭泣。
但她骨子里继承了母亲的坚韧。
她努力学习俄语,很快就融入了新的环境。
她在这里认识了很多和她一样背景的孩子,比如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、毛岸青,朱德的女儿朱敏等等。
他们在一起学习,一起生活,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这段特殊的经历,也让瞿独伊从小就养成了独立、坚强的性格。
1930年,瞿秋白和杨之华奉命回国,投身到更为艰险的地下工作中。
临行前,他们来到伊万诺沃,与女儿告别。
这一次的分别,瞿独伊已经隐隐感觉到,或许要很久很久才能再见。
她抱着父母不肯松手,眼泪打湿了瞿秋白的衣襟。
瞿秋白抚摸着她的头发,眼神里充满了不舍和歉疚。
「独伊,爸爸妈妈要去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你在苏联要好好学习,长大了,回国来建设我们的新中国。」
这成了父亲对她最后的嘱托。
父母走后,瞿独伊只能通过信件与他们联系。
那些来自遥远祖国的信,成了她最宝贵的精神慰藉。
信中,父亲会给她讲国内的革命形势,母亲会仔细询问她的生活和学习。
他们总是报喜不报忧,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她的爱和思念。
瞿独伊也将自己的思念写进回信里,寄往那个她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。
然而,这样的信件往来,在1934年之后,变得越来越稀少。
瞿独伊隐隐感到不安。
她从一些零星的消息中得知,国内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残酷。
直到1935年的夏天,那个改变她一生的噩耗,终于还是传来了。
那天,儿童院的院长把她叫到办公室,表情异常严肃。
他递给她一份来自共产国际的内部通报。
瞿独伊的俄语已经非常流利,但她看着那份通报上的铅字,却感觉每一个字母都像针一样,扎着她的眼睛。
通报的内容很简短,却字字千钧:

「中国共产党前领导人瞿秋白同志,因叛徒出卖,于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。在狱中坚贞不屈,已于近日英勇就义。」
那一瞬间,瞿独伊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
她手中的那张薄薄的纸片,变得有千钧之重。
她不相信,那个温文尔雅的父亲,那个教她俄语、给她讲故事的父亲,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。
她冲出办公室,在儿童院的白桦林里疯狂地奔跑,任由泪水模糊了双眼。
她多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。
父亲牺牲的细节,是在很久之后,她才陆续知道的。
他是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,因患有严重的肺病,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。
在转移途中,不幸被捕。
在狱中,国民党用尽了高官厚禄的诱降和严刑拷打的折磨,都未能让他屈服。
他写下了著名的《多余的话》,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与反思。
就义前,他神色自若,让刽子手为他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。
他盘膝而坐,含笑对刽子手说:「此地甚好。」
然后高唱着《国际歌》,从容就义,年仅36岁。
这些细节,像一把把刻刀,深深地刻在了瞿独伊的心里。
巨大的悲痛,并没有将这个14岁的少女击垮。
相反,一种强烈的责任感,在她的心中油然而生。
她要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,她要像父亲一样,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。
这之后,组织上安排她的母亲杨之华来到苏联。
母女二人在莫斯科重逢,抱头痛哭。
她们相互慰藉,相互支撑,在异国的土地上,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光。
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。
1941年,苏德战争爆发。
法西斯的战火,烧到了莫斯科的城下。
在苏联的中共党组织决定,安排一批在苏的同志和子女,经由新疆,返回延安。
瞿独伊和母亲杨之华,就在这批归国的名单之中。
她们满怀着回到祖国、投身抗战的热情,踏上了归途。
她们以为,这条路通往的是延安的窑洞和革命的圣地。
却未曾想到,在新疆,等待她们的,竟是另一座深不见底的牢狱。
当时的“新疆王”盛世才,表面上亲苏亲共,背地里却与国民党勾结,心怀鬼胎。
当瞿独伊和母亲一行人,乘坐着苏联派出的卡车,风尘仆仆地抵达新疆首府迪化(今乌鲁木齐)时,盛世才露出了他狰狞的面目。
他以“护送”为名,将这批一百多人的归国人员,全部软禁了起来。
不久之后,软禁升级为正式的逮捕。
瞿独伊、杨之华,以及同行的毛泽民(毛泽东的弟弟)、陈潭秋(中共创始人之一)等所有共产党员及家属,全部被投进了阴森的监狱。
那一年,瞿独伊20岁。
她最好的青春年华,将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度过。
新疆的监狱,条件极其恶劣。
阴暗、潮湿,虱子和臭虫遍地。
更可怕的,是无休止的审讯和精神折磨。
盛世才企图从这些共产党人身上,榨取所谓的“机密”,逼迫他们“脱党”,以作为自己向蒋介石献媚的投名状。
然而,他打错了算盘。
在狱中,由毛泽民、陈潭秋等人秘密组织起一个临时的党支部,带领大家与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。
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学习,相互鼓励。
年轻的瞿独伊,在斗争中迅速成长。
她利用自己精通俄语的优势,担任起狱中同志们的“俄语老师”,教大家唱苏联歌曲,鼓舞士气。
她和母亲杨之华住在一个牢房,母亲的沉着和坚毅,给了她巨大的力量。
最残酷的考验,发生在1943年。
丧心病狂的盛世才,秘密杀害了毛泽民、陈潭秋等一批重要的领导同志。
监狱里,一片白色恐怖。
敌人拿着伪造的“脱党声明”,挨个牢房地逼迫大家签字。
当他们走到瞿独伊和杨之华的牢房时,杨之华挺身而出,义正言辞地斥责道:
「我们是共产党员,我们是无罪的!要杀要剐随你们,但想让我们背叛信仰,永远也办不到!」
瞿独伊也昂着头,站在母亲身边,怒视着敌人。
在那一刻,她仿佛看到了父亲瞿秋白在长汀狱中,面对敌人劝降时傲然的身影。
父女二人的身影,在历史的时空中,奇迹般地重合了。
这场残酷的牢狱之灾,持续了整整四年。
直到1946年,抗战胜利后,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多方斡旋和大力营救下,被关押在新疆的这批幸存的共产党员,才终于重获自由。
当瞿独伊走出监狱,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时,她已经25岁了。
她的脸上,写满了与年龄不符的沧桑,但她的眼神,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亮和坚定。
她没有片刻的停留,立刻和同志们一起,踏上了前往延安的道路。

那里,有她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。
那里,有她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,在等待着她。
05
延安的宝塔山,黄土高原的风,以及同志们脸上洋溢的淳朴热情的笑容,都让从牢狱中归来的瞿独伊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。
在延安,她终于见到了许多传说中的领袖人物,听他们讲述着父亲瞿秋白过去的点点滴滴。
也是在1946年,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,瞿独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在入党仪式上,她抚摸着胸前的党徽,百感交集。
这是父亲的信仰,也是她的信仰。
为了这一天,她等待了太久。
由于她出色的俄语能力,组织上将她分配到了新华社工作。
在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,她成了一名新闻战线上的红色尖兵。
她翻译了大量的俄文稿件,向解放区军民介绍国际形势;她也把解放区的声音,把人民军队的胜利消息,翻译成俄文,向世界传播。
她的工作,平凡而重要。
时间很快来到了1949年。
新中国即将诞生,瞿独伊也跟随新华社的总部队,进入了刚刚解放的北平。
然后,就发生了开篇那一幕。
她被选中,担任开国大典的俄语播音员,这个看似偶然的选择,背后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必然。
她的家庭背景,她的特殊经历,她的语言天赋,以及她那颗对党无限忠诚的心,让她成为了这个光荣使命最合适的人选。
当她用那完美无瑕的第二遍录音,向世界宣告新中国的成立时,她的人生,也完成了一次与父亲跨越时空的交接。
开国大典之后,瞿独伊的人生,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1950年,她再次被派往莫斯科。
这一次,她的身份不再是革命者的女儿,而是新中国的外交和新闻工作者。
她的任务是,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。
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,在异国他乡白手起家,建立一个国家通讯社的分支机构,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。
但瞿独伊都一一克服了。
她既是记者,又是翻译,还是管理员。
在那段时期,她还多次担任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时的翻译。
她清晰、准确的翻译,严谨、细致的工作作风,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能够近距离地为敬爱的总理工作,也让瞿独伊感到无比的自豪。
1957年,瞿独伊从苏联回国。
之后的岁月里,她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新华社国际部工作。
无论在哪个岗位上,她都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,勤勤恳恳,兢兢业业。
她从不因为自己是瞿秋白的女儿而有任何的特殊要求,相反,她对自己要求得比任何人都要严格。
她把所有的精力,都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。
1982年,瞿独伊离职休养。
晚年的她,把更多的精力,放在了整理和撰写关于父母的回忆录上。
她觉得,自己有责任,把那段真实的历史,把父母那一代革命者的真实形象,告诉后人。
她写下了《我的父亲瞿秋白》、《母亲杨之华》等著作,用朴实而深情的笔触,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。
她笔下的瞿秋白,不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理论家,更是一个热爱生活、情感丰富的丈夫和父亲。
她笔下的杨之华,不仅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,更是一个在苦难中始终保持着优雅和乐观的奇女子。
在瞿独伊的客厅里,一直挂着一张瞿秋白就义前唯一的照片。
照片上的父亲,穿着中式对襟衣衫,背着双手,神情平静,目光深邃,嘴角还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。
瞿独伊每天都会看上很久。
她仿佛能从那张照片里,读懂父亲内心的从容和坚定。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。
曾经那个在开国大典播音室里,坚持重录一遍的年轻姑娘,也渐渐步入了晚年。
她亲眼见证了祖国从满目疮痍到繁荣昌盛的全部过程。
她实现了父亲的遗愿,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,屹立在世界的东方。
2021年,瞿独伊在北京逝世,享年100岁。
她的一生,跌宕起伏,充满了传奇色彩。
她是从上海滩的大家闺秀,到莫斯科的红色儿童;是从新疆的阶下囚,到开国大典的播音员;是从新中国的新闻官,到历史的记录者。
她的一百年,完整地见证了一个世纪的中国风云。
她的人生,就像一道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,承载着父辈的信仰,也传递着她自己的坚守,永远地回响在历史的天空中。
【参考资料来源】
瞿独伊:《我的父亲瞿秋白》杨之华:《忆秋白》《瞿秋白文集》中共党史出版社相关人物传记资料新华社相关历史档案及回忆录

